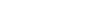联系我们
南昌绿瑞康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
联系人:肖总
电 话:13576919360
座 机:0791-88488287 88488626
微 信:13576272119
邮 箱:19406983@qq.com
地 址:青山湖区广州路2099号针织服装产业园一期2#-3厂房103
现在,如果在某聚会中随口问句“关注的事情是什么”,大多数人会把“食品安全”排在前几位。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,任何跟食品安全有关的说法 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,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广为传播。“解决食品安全问题”的呼声持续不断,有关部门也出台了项又项“措施”。然而,相关事件还是持续不断地出现。
消费者、主管部门和食品生产者,本应该是互相依存、互相制约、互相信任、互相促进的三角。然而,近几年来,公众的信任和信心或许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,不知道是将进步恶化还是触底反弹。
总而言之,在目前这种互相指责、互不信任的状况下,问题的解决将越加艰难。
有的问题允许漫长的等待,然而吃饭的问题,不能。
自供运动,能走多远?
2010年11月,据人民网报道:“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,部分省机关单位、大型国企、民营企业、上市公司、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,形成自供或特别食品基地。”
这种方式,大概可以称为“自供运动”。除了国家机关涉嫌滥用财政经费之外,商业机构和个人参与这种运动也无可厚非。任何特殊需求必然要付出特殊费用。对于商业机构和个人来说,“自供蔬菜”和昂贵品样,是富有者的消费方式。从另个角度说,这还有助于在保持耕种的前提下提高农村土地的商业价值。此外,许多“自供蔬菜”并非由租赁者自己耕种,而是雇农民来种的,倒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。
对于参与这种运动的小部分人来说,这种方式能够在定程度上解决问题。但是,从全社会的高度,这种方式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,作用实在有限。理由有三点:
先,这种方式的高成本注定了只有小部分人消费得起。生产规模越大,成本越低,在食品生产上尤其如此。虽然这种“”结构避免了中间的流通环节,但是个小规模的菜地,要种植品种多样的蔬菜,只能采取手工操作,人力成本可想而知。
其次,许多没有种过地的人,会很天真而固执地认为只要不用化肥和农药,问题就被解决了。他们并不知道“有机种植”远远不是那么简单。旦蔬菜长虫,不用农药的结果往往就是没有收成。多数土地不施肥很难长出蔬菜来。而使用“农家肥”的话,且不说如何获得那么多农家肥,施肥的人力成本则更高。此外,未经处理的“农家肥”并不意味着安全。相对于化肥或者经过工业处理的有机肥,农家肥携带的病菌同样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。
再者,对于城市中的般人,不大可能频繁地去城外打理菜地。即使是自己种的菜,也只能采摘之后进行存储。蔬菜的储藏处理,又会带来其他的安全隐患。如果只是租赁土地,雇农民种植,那么就跟定点采购类似。从报道来看,目前的“自供结构”主要还是依靠君子协议。旦发生纠纷,比如种出的蔬菜在数量和质量上达不成致,那么“放心菜”也就会吃得很“闹心”了。
城市化、现代化注定社会必然高度分工。对食品安全担忧,就“自供蔬菜”,那么对学校教育不满呢?对医疗服务不满呢?难不成都小规模地自己来?这其实就是过去的“企业办社会”模式。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,国家机关和企业自己管理养老、住房这样的问题效率很低。而食品问题甚至更加复杂繁琐,换个角度来想:即使企业愿意花足够的钱去为员工建立“基地”,可若是把那些钱分给员工的话会不会有更实惠的结果?
不考虑“自供运动”将会遇到的种种难题,光是成本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行之路。而且,食品安全不仅仅是蔬菜的问题。实际上, 那些“自己种地”生产不了,或者“自供”成本更加高昂的食品,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,比如加工食品、餐馆食品以及肉类等。
以商治商,是否找到出路?
目前在这种小打小闹的“自供运动”面临着许多潜在的问题,时间长了必然会暴露出来。它如果发展成“企业办社会”的模式,显然没有生命力。如果沿着现代化规模化,则可能发展成国外的IP模式或者FOP标签系统。IP是“Identity Preserved”的简称,有人翻译成“身份保持”。而FOP是“Front-of-Pack”的简称,指的是“以标志形式出现在包装盒上”。
IP模式的核心在于对食品生产过程进行“全程追踪”。从种子开始,经过种植、田间管理、收割、加工,直到消费者,整个过程都需要进行记录。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满足特定的要求,比如什么样的种子,使用什么样的肥料等,就可以获得IP认证。而FOP标签,在目前的美国是在产品包装上提供些营养评价方面的信息。面对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安全问题,这个FOP模式也完全可以扩展成安全方面的评价。
从结果上看,IP模式和FOP标签与“有机认证”、“绿色认证”有相似之处。不过,它们在运作上差异很大。“有机认证”和“绿色认证”是政府主导的,而IP模式和FOP标签则不定。它们更多的是“信用保证”,可以由行业联盟、专业协会甚至某个商业机构来进行。它们没有“官方”做担保,能否被消费者接受就完全取决于它们的信誉。在传统心理上,我们更希望“官方保证”。但是,相对于“官方认证”潜在的滥用和腐败,个需要自己建立信誉的认证体系并不见得更不可靠。
因为IP模式和FOP标签可以涵盖任何产品,以及产品的任何阶段,所以它不会受到“自供运动”难以避免的产品种类的制约。而规模增大,也使得其成本相对于“自供运动”产品要低。不过,与普通产品相比,这些产品的生产和认证依然需要相当的成本来维持。换句话说,消费者依然要为“放心”而付出更高的价格。
IP模式和FOP标签的势在于对于政府监管的依赖减弱了。它对食品安全的保障,是通过消费者“用钱投票”来实现。从根本上说,就是生产者和认证者通过生产“放心食品”来赚更多的钱,而消费者通过付出更多的钱来购买“安心”。
食品安全,谁来管理?
不管是“自供运动”,还是发展到层次的IP模式或者FOP标签,都需要通过消费者增加开销来获得“放心食品”。从社会成本来说,这是不必要的浪费。尤其是“自供模式”,本身就不是多数人能够承担的即使多数人能够承担,也没有那么多的土地资源来实现。
作为社会问题出现的食品安全,很难依靠个人的“明哲保身”来保障。社会问题,终还是要靠社会来解决。每个人都切身相关,政府部门也再“下决心”。为什么经过那么多人的努力,形势却没有好转,公众的不安甚至更加强烈呢?
食品安全事件的制造者都是食品生产者,所以他们承担公众的痛骂也是咎由自取。但痛骂毕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任何行业,存在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赚钱。好企业与坏企业的区别,不是谁有道德,而是谁赚钱的方式合理合法。我们可以推崇和赞赏那些“高尚”的商人,问题是把食品安全寄托于企业的“高尚”,就像是把公正廉明寄托在包青天身上样,完全不靠谱。
根本上说,生产者要赚的钱,掌握在消费者手中。赚钱的方式,就是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。理论上说,消费者才是决定生产者如何生产的人。比如说,当消费者味追求“便宜”,那么生产者就会提供“便宜”的产品。但是保障食品安全需要相当的成本,价格便宜了就必然要在某个方面捣鬼。肉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据报道,当年某个地区的肉松几乎全部都采用了劣质原料。即使偶尔有试图不随大流的生产者,也会很快被市场淘汰。“劣币驱逐良币”,在中国的食品市场是如此突出。三聚氰胺席卷全行业,则是另个典型的例子。
不过,单靠消费者自己,也解决不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问题。在多数情况下,消费者无力分辨产品是否合格,更不清楚低价的产品
是企业技术革新和“让利”的结果,还是造假的结果。即使消费者愿意为“放心食品”付出额外费用,还是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哪个产品是物有所值的。
所以,问题又回到原点: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,终还是要靠主管部门来推动。
主管部门,为什么只打雷没下雨
中国挨骂多的政府部门,可能就是食品管理的“有关部门”了。每次有关食品安全的事件出现,“有关部门”定会被口水淹没。
可能“有关部门”也很委屈 下的决心很多,干的工作也不少,为什么就没有起到相应效果?
公众和媒体喜欢说的话是“法制不健全”,经常是每出个事件,就呼吁“立法管管”。实际上,中国跟食品安全有关的法规并没有大的问题,在很多具体规定上,甚至比美国、加拿大等还要保守和严格。过去的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,都可以在当时的法规框架内解决。只是,法规只能提供纸面上的保护当“有法不依,违法不究”的时候,“有法可依”的结果就是“吓死胆小的,撑死胆大的”。
就具体的监管体系来说,中国目前这种多个部门“分段管理”的体制问题重重。是否禁用种食品添加剂,要由6个部委参与决策,“科学决策”就很容易被“部门利益”的扯皮边缘化。在实际运作中,也就必然产生灰色地带看起来有多个部门“可以”管理,同时也就意味着每个部门都可以等着别的部门去管理。经常有这样的报道:为了某个事件,记者向A部门询问,被打发到B部门;向B部门询问,被打发到C部门绕了圈,可能又被打发回A部门。
即使“有关部门”想管,中国的市场现实同样使得监管困难重重。美国的大型养鸡场提供了99%的鸡蛋,所以只要控制了他们,市场上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安全事故。对于那些小型的养鸡场,政府反倒管得不那么严。而中国的食品生产和流通是由大量小规模的从业者主导的。要对他们实施严格监督,执法成本可想而知。
更麻烦的还在于,这些部门都是某政府的下属 也就意味着,他们要“配合”当地政府的“大局” 城市形象、财政收入、就业等。任何负面新闻出现,都可能被“大局”所“和谐”。所以,小生产者可能受到监管处罚,但是倒下了个,可能会站起来群。而个生产者如果做成了“大企业”,主管部门也就未必能够对它进行监管。即使它们有违法行为,只要没有出现人神共愤的结果,当地政府就不希望“影响企业运作”,甚至会进行“特别关照”。“谁找某某企业的麻烦,我就找谁的麻烦” 些地方政府脑把这样的口号当作对辖区内大企业的支持。“有关部门”在想要查处这样的企业之前,不得不三思是不是会被上司当作“找麻烦”。像三聚氰胺的使用,据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,至少在出口宠物食品致死动物之后,主管部门不应该不知道它的非法使用。但是,在当地政府“挥泪斩马谡”之前,当地的“有关部门”是工作疏忽没有发现问题,还是迫于“大局”不敢管?
三方互动,才是答案
消费者、生产者和主管部门,构成了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三角。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哪个方面或者哪个部门单努力就能够解决的。只有三方形成良好的活动互信,才能够建立规范的市场。消费者付出合理的价格获得放心的食品,生产者通过生产合格的产品赢得利润,而管理者,则通过严格致的执法来实现“劣币淘汰”、“良币流通”。
当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开展“自供运动”的时候,其实已经做好了“用钱投票”的准备。而生产者,看到合法生产的商机了吗?管理者,又做好了“只为食品安全负责,不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”的准备了吗
生活中,我们经常听到“某某食物中的某有害物质超标了多少多少”的说法。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:同种有害物质,在同种食物中,不同国家的“安全标准”不尽相同。这就产生了种“荒诞”的结果:有害物质在某个含量的种食物,在个国家是“安全”的,在另个国家却是“有害”的。
“安全标准”的意义,是低于它就“安全”,超过它就“有害”么?要回答这个问题,先得知道“安全线”是如何划定的。
问题:人体能够承受多少?
任何有毒有害物质,都需要在定的量下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。要建立食物中的“安全标准”,先要知道人体能够承受多少的量。理想情况下,是要找到这样个量:当人体摄入的这种物质低于这个量时,就不会受到损害;而高于这个量,就有定的风险。该量被定义为“无可测不利影响水平”(NOAEL)。
在实际操作中,“无可测不利影响水平”的确定并不容易。先,“损害”如何界定?人体有各种生理指标,每项指标都有正常的波动范围,如何来判断发生了“损害”呢?其次,出于人类的伦理,我们不能明知种物质对人体有害,还拿人来做实验,让实验者吃到受害的地步。
多数情况下,是用动物来做实验。先,喂给动物定量的目标物质,跟踪它在体内的代谢和排除情况。如果该物质很快被排出,那么问题就要简单些。在定的时间内(比如几个月)喂动物不同的量,检测各项生理指标,以没有出现任何生理指标异常的那个量为动物的“大安全摄入量”。如果这种物质在体内有积累,就比较麻烦,需要考虑在体内积累到什么量会产生危害,然后再计算每天每千克体重能够承受的大量。考虑到动物和人的不同,需要把这个量转化成每千克体重的量,再除以个安全系数(通常是几十到百,有时甚至更高),来作为人的“安全摄入量”。比如说,用某种物质喂老鼠,几个月之后,每天喂的量少于10毫克的那组老鼠都没有问题,而喂20毫克的那组老鼠中有两只出现了不良反应,那么10毫克就是这次试验得到的“安全上限”。假如这些老鼠的平均体重是100克,那么每千克体重能够承受的量就是100毫克。然后用这个数据来估算针对人的“安全上限”:如果采用100的安全系数,那么“安全标准”就定为每千克体重1毫克;如果采用50作为安全系数,“安全标准”就定位每千克体重2毫克。
有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有比较多的研究数据。比如镉,在通过饮食进入人体的情况下先出现的伤害在肾脏。镉会在肾脏累积,肾皮质中的镉含量跟肾脏受损状况直接相关。当肾皮质中的镉含量在每千克200毫克时,大约有10%的人会出现“可观测到的不利影响”。卫生组织把这个含量的四分之,即每千克50毫克,作为“安全上限”。然后考虑到饮食中镉的平均吸收率,以及能够排出的部分镉,计算出每周每千克体重吸收的镉在7微克以下时,对人体没有可检测到的损害。这个量叫作“暂定每周耐受量”(provisional tolerable weekly intake,PTWI)。平均来说,这个量与每天每千克体重不超过1微克是样的。对于个60千克的人,相当于平均每天不超过60微克。世卫组织采用这个“每周”的时间基准,是为了更好地表达“平均”的意思 比如说,如果现在吃了90微克,而明天控制到30微克,那么就跟两天各吃了60微克是样的。
还有些有毒物质对人体的危害缺乏直接实验数据,对于动物的危害结果也是在大剂量下得到的。而通过饮食都是“小剂量长期摄入”,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危害,就没有实验数据。科学家们会采用“大剂量”下得到的实验数据,来“估算”在小剂量长期摄入的情况下对人体的影响,从而制定“安全标准”。这种“安全标准”就更加粗略,终得到的数字跟采用的模型和算法密切相关。比如烧烤会产生种叫做苯并芘的物质,在动物和体外细胞实验中体现了致癌作用。这种物质在天然水中也广泛存在,而在饮用水中的浓度范围内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致癌风险,还缺乏数据。根据已知的数据进行模型估算,如果辈子饮用苯并芘浓度为每千克0.2微克的水,增加的癌症风险在万分之的量。所以,美国主管机构设定饮用水中的苯并芘“目标含量”是零,而“实际控制量”则是每千克0.2微克。
问题二:特定食物中允许存在多少?
知道了人体对于某种物质的“安全耐受量”,就可以指定它在某种食物中的“安全标准”了。
有的有害物质几乎只来源于某种特定的食物,那么就用“每日大耐受量”除以正常人会在天之中吃的大量作为“安全标准”。比如有种叫做“莱克多巴胺”的瘦肉精,进行过人体试验,在每天每千克体重67微克的剂量下没有出现不良反应。美国采用50的安全系数,把每天每千克体重1.25微克作为普通人群的NOAEL值。假设个50千克的人每天要吃100克猪肉,得到猪肉中的允许残留量为每千克625微克。
有的有害物质则存在于多种食物中。比如镉,大米是大来源,按照每千克体重每天1微克的“安全限”,个60千克的人每天可以摄入60微克。假设大米中的镉含量是每千克200微克(即中国国家标准的0.2毫克),那么每天不超过300克大米,就还在“安全限”之下。此外,水和其他食物也是可能的来源。世卫组织认为来自于饮水的镉不应该超过“安全标准”的10%,假设个60千克的人每天摄入两升水,因此把引用水中镉的安全标准定为每升3微克。
问题三:如何理解“安全标准”?
显而易见,所谓的“安全标准”是人为制定的。制定的依据是目前所获得的实验数据。当有新的实验数据发现在更低的剂量下也会产生危害,那么这些“安全标准”就会相应修改。比如镉,些初步实验显示在目前设定的安全量下,也有可能导致肾小管功能失调。如果在进步的实验中,结果被确认,那么镉的“安全限”就会相应调低。
此外,安全标准的设置中都会使用个“安全系数”。具体采用多大的系数,也是人为选择的。不确定性越大,所选择的安全系数也就越大。仍然以镉为例,制定标准是基于生理指标,4的安全系数就可以了。而莱克多巴胺,制定基准是6名志愿者的宏观表现,推广到全体人群的不确定性就比较大。在制定莱克多巴胺安全标准的时候,美国采用的安全系数是50,而得到每千克猪肉50微克的标准。世卫组织和加拿大的安全系数就要高些,后得到的标准是每千克40微克。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更为保守,采用的标准是每千克10微克。中国则采用是“零容忍”,完全不允许存在。
安全标准的制定还与人群中对该种食物的普遍食用量有关。比如说无机砷,世卫组织制定的安全上限是每天每千克体重2微克,相当于60千克的人每天120微克。在欧美,人们吃的米饭不多,很难超过这个量,也就没有对大米中的无机砷作出规定。而在中国,大米是主粮,就规定了每千克150微克的“安全上限”。或许基于类似的原因,日本大米中镉的“安全限”就比中国的要高,是每千克400微克。
不难看出,这些“安全限”只是个“控制标准”,并不是“安全”与“有害”的分界线。比如说,如果个体重60千克的人,每天吃500克每千克含0.15毫克镉的大米,是“超标”的;而如果只吃200克每千克含0.25毫克镉的大米,则处在“安全范围”。这就好比考试,总需要个“及格线” 考了60分的人通过,考了59分的人重修,但这并不意味着得60分的人和得59分的人就有根本的差别。
每天大量吃红肉(指猪肉、牛肉和羊肉)会增加癌症风险,平均每天吃140克的人比每天吃30克以下的人结肠癌风险高30%左右。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个风险已经很大,所以愿意为了健康放弃吃这些肉。